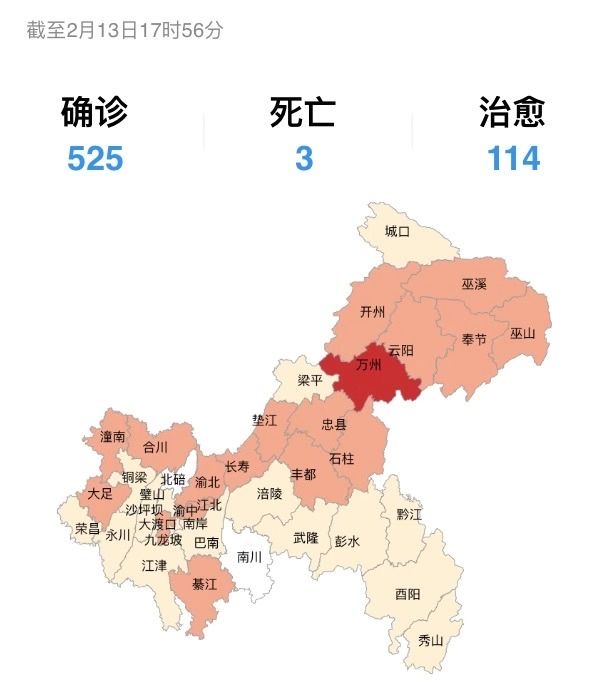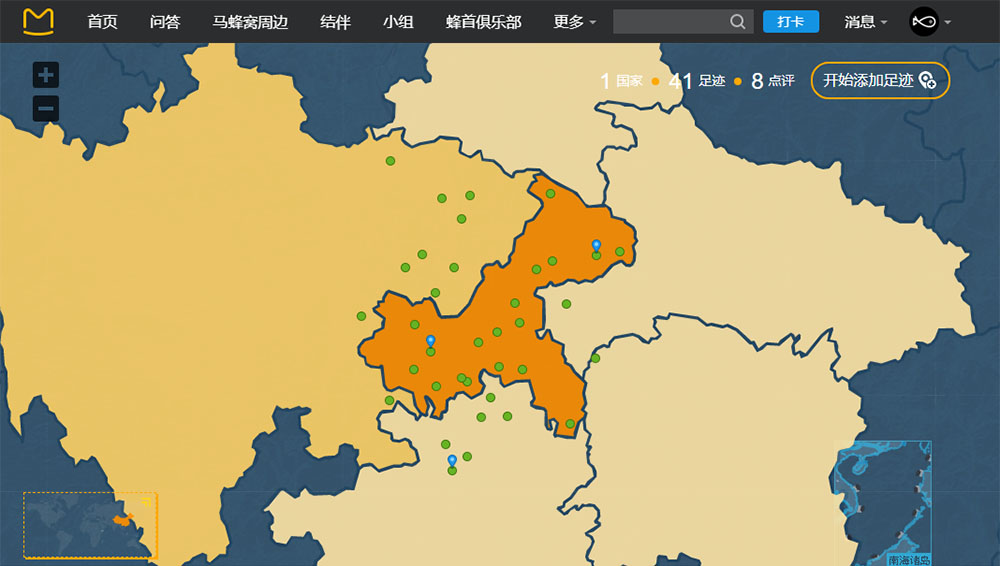还有半月VPS到期,因为AWS有了香港节点,所以打算后退半步,离家国更近一些,但是一想到满屏DOS命令乱飞的场景就懵逼,天生反感命令行的人换服务器是真的很折腾啊,起码要掉我半格血。但还是必须得换,因为服务器PHP版本低了,Wordpress的最新版本已经升级不了,单升PHP呢试了几次都没成功,那反正都要重装系统……不若先挪一下了。可懒人遇上强迫症,这动与不动的其实也好纠结的说,呵呵。
最近游记开始喜欢放视频,因为发现有时候图文的表现力确实缺乏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,所以尽管装备不好技术也渣,但偶尔也会随手录一些Vlog,不过以前都是搁硬盘里自我欣赏和回味了。现在自觉反正一天闲得蛋疼,然后玩单反这么久技术水平再一点儿长进木有,那不如学学视频剪辑吧。毕竟现在是Vlog的时代,不玩抖音快手,发个朋友圈视频太菜好像也挺掉我逼格不是?呵呵。
可博客放视频就有一个问题了,流量是个人难以承受之重。免费的视频网站广告时长让人难受,放自己服务器上呢,兜里没银子也是心惊肉跳的赶脚。所以权衡之后,我把尽量压缩到很小的视频放到了七牛那边,可结果没两天免费流量还是爆表,超了400%,一条短信过来就要我充值付账,吓我好一大跳!好在就只一碗面的价格,不然心里肯定会流血,但还是赶紧又换回腾讯的内容源了……你们难受,总好过我难受嘛,谁叫我穷撒?哈哈。
设计废了,码字不行,要不是爱玩,隔三差五还有两篇游记,我这一亩三分地也就算彻底荒了。
说到写游记,也扯得我蛋疼。知道自己风格没几人喜欢,所以之前纯属自娱自乐,也就是方便自己日后回忆追溯的。但突然某天从某篇文章开始就爆了,公众号二三十个活粉也能有好几K的阅读率,头条号里每篇文章的推送都是10W+(虽然离10W+的阅读还差十万八千里),但就算只有一两万的阅读也好过我孤芳自赏,也是我心甚悦的嘛。不到四百粉,头条还主动给了我一个V。于是心里一时踌躇满志,想着既然有人看了,那就以后尝试换换风格?好好写,用心写……结果我这还没开始使劲架篾呢,因为某篇文章里的视频可能被人举报而删文了,然后就进了小黑屋,之后的文章推送就几等于零。这剧情反转实在太强烈,我震精了,有些合不拢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