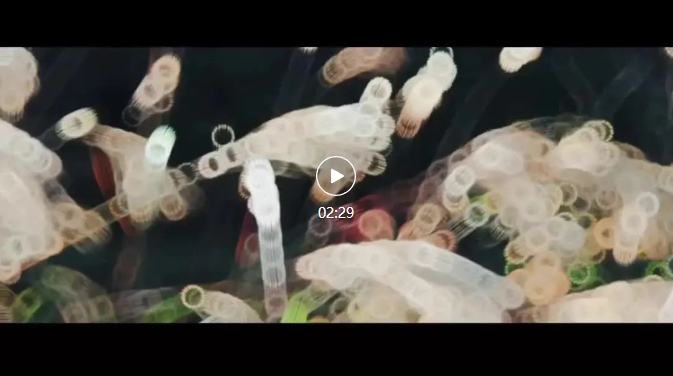
“鬼王山下,团凼河畔……”
这是水江镇中小学生考试时惯常使用的“八股文”必杀技之第一板斧。就跟圣旨“奉天承运,皇帝诏曰”一样,所谓开门见山,如果没有这一句话起头,好多人的作文似乎就写不下去。
某亦如此。二十多年以后,纸墨铺陈,依然难逃桎梏。


我也想不落窠臼,但到底还是俗人一个,常在河边走嘛……寻常人走过那寻常阡陌。
我游过无数次的河,我走过无数次的桥,好像都没变,又好像全都变了。岁月如歌,青春似河,当年我第一次听到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,也不自觉湿了眼眶来着。
一万个人有一万种乡愁!我的乡愁,是鬼王山下的风,是团凼桥下的河。

远香近臭,儿嫌母丑。这些年我寻桥无数,也曾多次提及家门口的龙见桥和团凼桥(积善桥),却也是从来不曾好生编排过。原因还真就是觉得她们太丑,太过稀松平常的缘故,呵呵。
人生如戏如局,孰能无过?焉能不惑?
要不是几年前,在网上看到一位远在上海的九十多岁(如果还健在,今年该一百岁了)的郑老太爷图文描摹他记忆中的南川和水江故乡风景,我还真没注意过团凼桥原来是一座廊桥来着。哪怕就在我眼皮子底下,哪怕桥墩上的痕迹如此明显,南来北往,过客无数,依然谁都视若无睹!

我想当然的以为廊桥可能毁在建国初期,解放军剿匪的时候。结果前段时间与舅舅闲聊,他说这廊桥他年轻时也曾见过,和水江场口的大小牌坊一样,悉数毁于文革。特么的,我差点儿哭晕在厕所,这算不算故意歧视我们八零后?
遥想六七十年代,胶片相机虽贵却也并非那么遥不可及。突然好想求助万能的互联网——有没有哪位水江的叔叔孃孃、公公婆婆,或者当年下乡的知识青年,彼时你们青春年少风华正茂,手里恰好就有团凼桥和老场牌坊的旧照?
我只看一眼!一眼就够!


子在川上曰:“逝者如斯夫。”山河依旧,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。
团凼桥下的水碾遗址还在,只是谁又能想起当年正在桥头碾米,而被土匪偷袭牺牲的解放军来着?耳熟能详的水江区长石乐斋,他和他的剿匪传奇,也好像一颗颗石子被丢进了団凼河。扑通,扑通……有点儿声响,有点儿浪花,但是都不大,而且还很快随波逐流,被泥沙掩盖,被前浪和后浪淹没。
说什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,团凼桥建桥两百年,过江之鲫犹如恒河沙数。在时间的长河里,谁都不过是沧海一粟!


一只螃蟹,最终可能会老死在家门口。
一只蜗牛,终其一生也爬不出半里地。
关于跬步与江河湖海的距离,我以为古人的步长和现代人是明显不一样的,或者说度量衡的差距其实蛮大。
团凼桥(积善桥),龙见桥下五里,嘉庆十年(1805)建。
事实上,龙见桥与团凼桥两桥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只有一千米,就算曲水流觞,沿着河曲漫溯那也只多五百米。但就是这一千五百米的距离,几乎囊括了我整个童年与青春所有的光影蒙太奇。
我在河边放牛,我在河里洗澡。偷过包谷,烧过红苕,折过杨柳,抚过竹笛……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分手和相遇!


老子说:“夫唯不争,水利万物。”
木心说:“从前书信很慢,车马很远,一生只爱一个人。”
岁月流金,从龙见桥到团凼桥,碧波荡漾里的旧时光,好像永远有那么一只小纸船停留在心上。青春呵常把万里扶摇,落魄呢又常把中年邮回家乡……“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”!这山一程水一程,一个人又一个人,昨日像那东流水,二十年,南柯一梦枕黄粱。

再也找不到童年的阿娇,外婆也已经不见好多年了,但我依然还能摇啊摇到外婆桥。
我的外婆桥真的就叫小桥,而几十米开外的大桥便是龙见桥。当鱼泉河的水与螃蟹塘来的水,在这里交汇,再往下便有了团凼河和团凼桥,我几十年也走不出去的地方。
一座山,两条河,三座桥,涓涓汩汩,浩浩汤汤,始终寄托着无数水江人的乡愁与梦想,亿万斯年,地老天荒。

“半生风雨半身寒,一杯浊酒敬流年。”那些我依然能够如数家珍的地名……小桥往上犹叫海洋溪,大桥往上也叫哀河,而我家如今也搬到了海洋石(寺)附近。这要是换作当年,大人眼皮子底下,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怕是再也不敢偷偷下水,下河洗澡了吧?
当年觉得河水很深很深,海洋石和“十米跳台”也很高很高,可如今水浅的地方都盖不过脚背,而河岸也佝偻得像个老头儿一样。
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。关于乡愁,就像溺水,那些年,那些人,那些事……再也回不去啦!